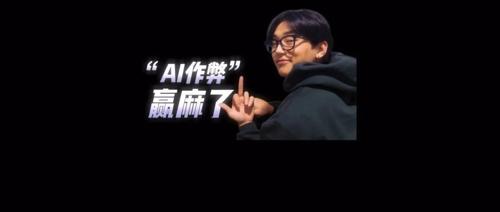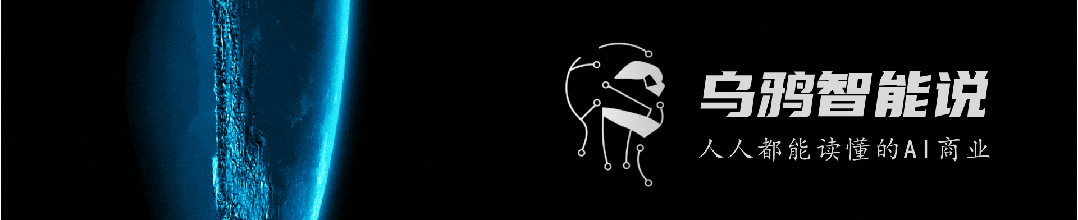
当绝大多数AI创业者还在思考“怎么做出一个好产品”,Cluely的创始人Roy Lee却另辟蹊径:把分发当成头等大事。
他的思路很简单——把分发做对,一切自然会随之而来。
Roy Lee的自信源于他所取得的成功。此前,Roy Lee曾靠着卖自己的AI作弊工具“Interview Coder”,在短短50天里,就赚了22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00万左右。
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他对于传播的运用。他不仅没有规避“作弊”这一高争议词,反而将其作为传播杠杆,每次质疑都会来一波流量。最终,虽然差评率高达50%,但这个产品视频在TikTok上突破2000万播放。
为此,Cluely还拿到了来自a16z的1500万美元融资。
谈到投资Cluely的理由,a16z解释是:
当大模型能力逐渐趋同,最值钱的不再是模型能力本身,而是谁能掌握用户的注意力分发权。
a16z看重Cluely团队的“分发实力”和“品牌认知能力”,认为其模式具有强复用性与放大效应。
不久前,a16z合伙人Bryan Kim、Erik Torenberg就与Roy Lee展开了一场对话,示了Cluely如何靠10周时间、10亿次曝光,颠覆了AI时代的创业剧本。
/ 01 /
跌出名校,走上最“好玩”的路
Roy Lee 的创业旅程,从来不是一条线性路径。高中时他因为“太出格”被同学举报,最终错失哈佛学籍。父母是大学申请咨询公司的老板,却没能保住自家儿子的常春藤身份——这是讽刺的开始,也是他个性确立的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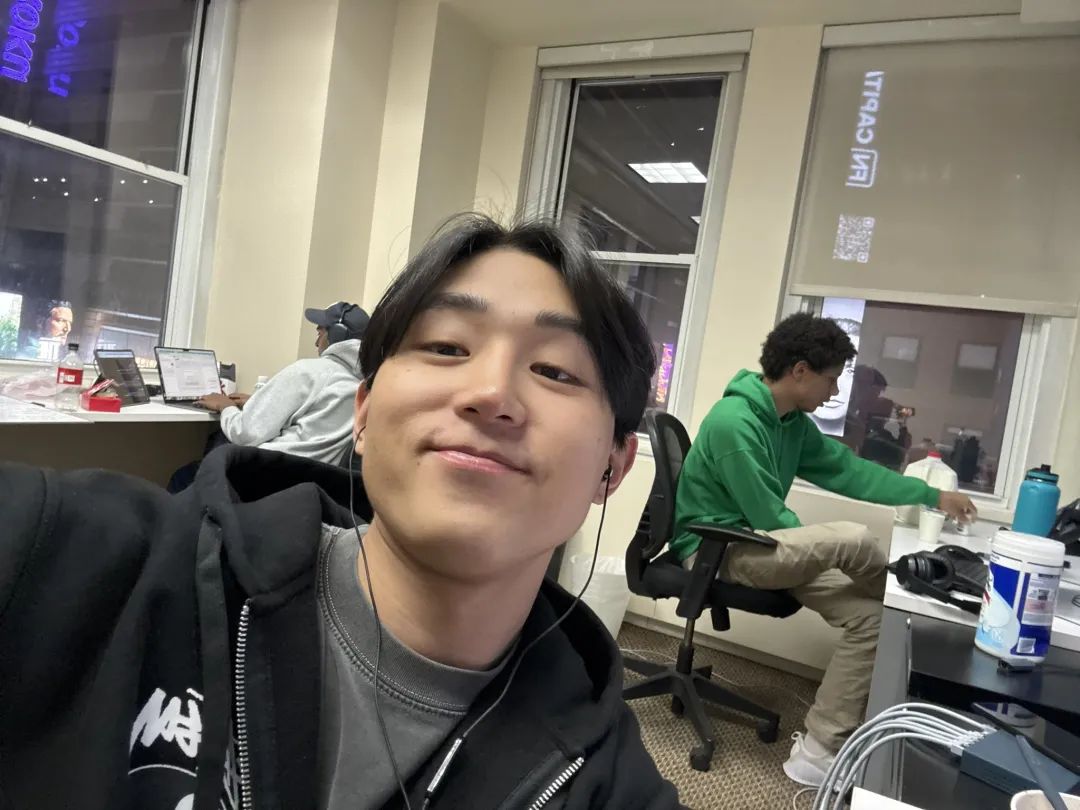
他说:“我一直是那个说出所有脑子里疯狂想法的人。”被停学、重新申请学校、读社区大学、进入哥大,再次退学创办 Cluely——Roy的人生像是一组“教育失败”的案例,但又精准地印证了那个在创业界流传的经典说法:
最好的创始人,往往来自边缘状态。
他也没掩饰自己的野心:“我上哥大的目的就两件事:找联合创始人,找结婚对象。现在还在找后者。”
他是典型的“系统外创始人”:不接受学院秩序,擅长制造注意力,主动利用制度摩擦作为流量杠杆。
/ 02 /
Cluely的真正产品是分发本身
Cluely 的产品,从来不是“一个功能集合”,而是“一个分发系统”——或者用 Roy 的话说,是“一个用内容获取使用数据,反过来定义产品形态的试验场”。
第一款产品 Interview Coder,是一个用来“在技术面试中作弊”的工具。它的诞生方式本身就是一次反常规的分发实验:
在宿舍写完,拍了一条挑衅式短视频,一夜之间上亿播放、登上 Hacker News 热榜,也被各大科技公司拉入封杀名单。视频被封、账号被举报、Roy 被哥大再次约谈。但同时,Cluely 的产品冷启动完成,第一批用户自然到来。
于是,Cluely的产品迭代逻辑确立:内容先行,产品跟随;用户先用,数据决定。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盲测产品。我们甚至不做用户访谈,直接看数据就行了。”
他们的内容策略像“分发雷达”:发布100条短视频,找到10条带来真实使用行为的素材;再围绕那10条做产品调整和新一轮内容试探,直到跑出“愿意持续使用”的方向。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市场契合”,而是一种“内容-市场-行为”的反向共建机制。
/ 03 /
分发为王,势头即护城河
传统科技公司的护城河,来自技术壁垒、平台优势或数据网络效应。但在 AI 初期阶段,这些都尚未成型。Bryan Kim提出了另一个关键概念:“在AI应用领域,势头本身就是护城河。”
原因很简单:
-
模型更新极快,工具功能趋同,产品难以建立长期优势;
-
用户分发依赖注意力获取,而非单点功能差异;
-
内容制造势头,势头制造认知边界。
Cluely 的做法正是构建“势能飞轮”:内容制造话题,话题制造认知,认知制造点击,点击制造使用,使用制造数据,数据回馈内容。
他们甚至提出一个极端观点:“如果你的营销负责人粉丝不到10万,就该换人了。”不是开玩笑,而是反映了他们对“知名度资产”的结构性理解。
“今天的产品,不是你有多强,而是别人有没有听过你。”
/ 04 /
组织结构:双主线,高密度实验
Cluely 只招两类人:能写代码的工程师,能做传播的创作者。
他们曾雇佣60多位兼职内容实习生,每人每天产出3条视频,在 TikTok、Instagram、YouTube Shorts 三个平台做并行分发。所有内容挂载产品链接,直接测算点击与转化数据。
Roy的思路是“高密度内容实验”:一天测几十条 CTA(行动引导),每周做一次“爆款复制”,每月基于结果调整 landing page 与产品功能。
这不是“用户增长部门”,而是“内容工厂+软件工厂”的混合系统。
“你为超级碗广告花几百万,我们花两万做内容,就能打出相同的曝光效果。”
Cluely本质是一个“由算法定义产品”的公司。他们的逻辑是:
“最便宜的用户研究方式,是让内容被算法推荐,然后看谁点击、谁留下、谁转化。”
/ 05 /
产品愿景:液态AI覆盖层
Cluely 的终极愿景,不是一个插件,也不是一个 Copilot,而是一种“液态 AI 覆盖层”的存在。
Roy 把它比喻成“玻璃水”:你感觉不到它启动,也不需要点击,它只是悄悄覆盖在你日常操作之上,根据鼠标路径、输入意图和上下文环境提供协助。
“未来的 AI,不会打断用户,而是悄悄帮助。”
这种体验逻辑区别于 OpenAI、Rewind、Cursor 等 Copilot 式工具。它不是回答你的问题,而是理解你的状态,预判你的需求。
“你不会觉得你在跟一个 AI 聊天,而是你突然觉得某个按钮刚刚好出现在你需要它的位置。”
他们想做的是 UI 层的革新:把 Copilot 从“助手”变成“第一视觉层”,从“功能面板”变成“行动暗示”。
/ 06 /
Rizz营销:真诚 + 敢言 + 自带争议
Roy 另一个标签,是“敢说”。他提出的“Rizz营销”哲学,被很多人视为争议制造。他不避讳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做内容开头,也不担心在镜头前说出“不政治正确”的话。
但这些不是“风格化表演”,而是结构性传播手段。他的底层逻辑是:
-
平台偏爱情绪;
-
用户停留来自冲突;
-
分发需要摩擦;
“这个世界不缺正确的观点,缺的是你不说点过头话,谁理你?”
而当这些话成为评论区的燃料、成为YouTube的二创、成为推特的转发截图时,势能也就开始了。
Roy的终极公式是:
真诚+态度+一点争议感=分发最大化。
/ 07 /
尾声|如果 Cluely 赢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Torenberg 在对话尾声问道:“如果 Cluely 赢了,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Roy 没直接回答,但我们或许已经知道答案:
-
创业者先是内容人,然后才是产品人;
-
产品不再从需求开始,而从分发开始;
-
公司不是雇人干活,而是建系统制造流;
-
软件创业的起点,从 build → sell,反转成 sell → build;
Bryan Kim 总结说得很克制却深刻:
“最有趣的结果,往往就是最可能的结果。”
Cluely,也许是那个结果的前奏。
PS:如果你对AI大模型领域有独特的看法,欢迎扫码加入我们的大模型交流群。

(文:乌鸦智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