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 6 月 30 日,马克·扎克伯格向 Meta 员工介绍了新的超级智能团队(MSL)。CNCB 获得的备忘录列出了最近招聘的员工名单及其简介,其中许多人来自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等竞争对手的 AI 公司。消息人士表示,尽管 Anthropic 也是 Meta 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与 Meta 的文化不太契合。
扎克伯格在周一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将把我们的整个组织架构称为‘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MSL)。这包括我们所有的基础研究团队、产品团队和 FAIR 团队,以及一个新的专注于开发下一代模型的实验室。”
原 Scale AI CEO Alexandr Wang 将领导 Meta 的超级智能实验室,Meta 此前已以 143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该公司。前 GitHub CEO Nat Friedman 将与 Wang 共同领导该部门,主要负责 Meta AI 产品和应用研究工作。备忘录显示,目前 Friedman 并未与 Meta 此前 AI 产品团队负责人Connor Hayes 有明确的分工。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目前共 11 名成员,以下是根据扎克伯格备忘录整理的新聘人员名单:
-
Trapit Bansal,OpenAI 技术联合创建者,开创思维链强化学习(RL on chain of thought)技术,主导 O 系列模型研发。
-
Shuchao Bi,GPT-4o 语音模式与 o4-mini 技术联合创建者,曾任 OpenAI 多模态后训练负责人。
-
Huiwen Chang,GPT-4o 图像生成技术联合创建者,在谷歌研究院任职时构建了 MaskIT 及 Muse 文生图架构。
-
Ji Lin,深度参与开发 o3/o4-mini、GPT-4o、GPT-4.1/4.5、40-imagegen 及 Operator 推理框架。
-
Joel Pobar,Anthropic 推理技术专家,此前在 Meta 工作 11 年,主导 HHVM、Hack、Flow 等开发及机器学习工具优化。
-
Jack Rae,Gemini 预训练技术负责人、Gemini 2.5 推理架构设计者,DeepMind 任职时期主导 Gopher/Chinchilla 早期大模型研发。
-
Hongyu Ren,GPT-4o、4o-mini 等 O 系列模型技术联合创建者,曾任 OpenAI 后训练团队负责人。
-
Johan Schalkwyk,前 Google Fellow,Sesame 语音助手早期开发者,Maya 项目技术负责人。
-
Pei Sun,谷歌 DeepMind Gemini 后训练 / 编码 / 推理核心成员,Waymo 两代感知模型架构师。
-
Jiahui Yu,o3、o4-mini、GPT-4.1/4o 技术联合创建者,曾任 OpenAI 感知团队负责人,Gemini 多模态技术联合主管。
-
Shengjia Zhao,ChatGPT、GPT-4、全系 mini 模型及 4.1/o3 技术联合创建者,OpenAI 合成数据团队前负责人。
MenloVentures VC Deedy 在 x 上表示,他们每年的薪酬待遇在 1000 万美元以上。
这个团队中亚洲人(更准确说是华人)占了大多数,有网友对此评价道,“2025 年是亚洲人(非 Agent)之年”。

值得注意的是,Meta 更早时候从 OpenAI 苏黎世研究团队挖来的 Lucas Beyer、Alexander Kolesnikov 和 Xiaohua Zhai 并不在该实验室。据悉,这三人去年年底才在苏黎世设立了 OpenAI 办公室。
“过去数月我密集地与 Meta 内部精英、顶尖 AI 实验室成员及潜力初创团队成员见面,组建了这个小项目的核心创始小组。我们仍在组建这个团队,并将继续邀请 AI 组织中的一些人加入这个实验室。”扎克伯格还在备忘中提到,Meta 已启动下一代模型的研发工作,目标在未来一年左右达到技术前沿水平。
根据备忘录,扎克伯格的人才争夺会持续上演。
为了应对这场人才争夺战,OpenAI 首席研究官 Mark Chen 上周六向员工发送了措辞强硬的备忘录,誓言将与这家社交巨头正面交锋。此前,扎克伯格刚刚成功从该公司挖走了四名资深研究员。这四位都是华人研究员,也在此次公布的超级实验室团队成员名单中,分别是 Jiahui Yu、Shuchao Bi、Shengjia Zhao 和 Hongyu Ren。
“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像是有人闯入我们家偷了东西一样。请相信我们绝不会坐以待毙。”Chen 说道。
他承诺正与 OpenAI CEO Sam Altman 以及公司其他领导人“全天候地与那些收到录用通知的人进行沟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我们正在重新调整薪酬体系,并规划创新方案来表彰和奖励顶尖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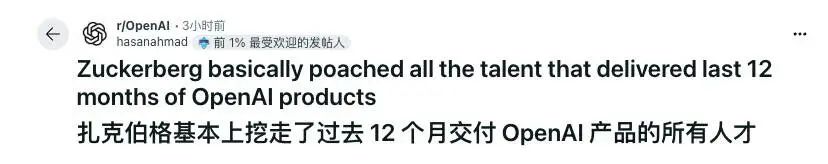
Altman 在与其兄弟 Jack Altman 的播客中表示,扎克伯格的招人方式十分激进,他已经向部分 OpenAI 员工提供了 1 亿美元的签约奖金。但当时 Altman 表示,OpenAI 的核心技术团队无一人跳槽。

按照媒体爆料,Meta 给的签约奖金依然可能是“改变人生”的量级——一次性就能让人财务自由,年薪都不用算。虽然 Lucas 否认有 1 亿奖金,但在业内人士眼中,这已不重要,关键是 这场战役的“军备竞赛”模式已经开启。
而真正让 OpenAI 感到威胁的,恐怕并不是某几位个别离职员工,而是背后整个 AI 人才市场的“泡沫膨胀”。正如一位投资人所言:“现在的顶尖 AI 研究员,不管原本年薪是多少,总有人愿意出 50 倍来挖。”
在备忘录中,OpenAI 七名研究负责人联合挽留员工。其中,一位负责人鼓励员工收到 Meta 录用通知后主动联系他们:“如果他们给你施加压力,或者开出离谱的超高薪酬,就让他们放弃吧。在可能最重要的决定面前给别人施加压力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据悉,OpenAI 员工正努力应对繁重的工作量,许多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长达 80 小时。多位消息人士透露,OpenAI 这周将基本停工,以便让员工有时间恢复精力,但高管们仍计划继续工作。
“Meta 知道我们这周要休整,肯定会利用这段时间试图给你们施加压力,让你们快速独立地做出决定。如果你感到压力,别害怕联系我。我和 Mark 一直在你身边,愿意支持你!”Meta 的另一位领导写道。
虽重视 Meta 的举动,但 Chen 也指出公司“过于陷入定期产品发布的节奏和与对手的短期比较”。此前就有前员工爆料,Altman 过去要求每几个月就要有轰动性的发布,但他现在似乎更聚焦实现 AGI。
“我们需要继续专注于真正的目标,那就是找到将计算(今年晚些时候将有更多超级计算机上线)转化为智能的方法,这是主线任务,”Chen 写道,“要记住,与 Meta 的冲突只是支线任务。”
扎克伯格的“洋基队打法”:
要么称王,要么内耗崩盘
在 Meta 的超级实验室计划逐步成型之际,业界也在紧盯这一“战队”是否真能出成绩。扎克伯格押注的,是一种典型的“洋基队式策略”:用几乎不设上限的预算,组建一支由世界顶尖研究员构成的“梦之队”。
这种高密度的天才聚合,理论上能产生奇迹,但也伴随着高风险。与 OpenAI 的人才出走形成对比的是,Meta 团队如今被推上了巨大的舆论与组织压力。曾任职于谷歌、Facebook、微软、苹果等企业的并购交易主管 Jordan Thibodeau 在最近的一个采访中直言:“新人团队成员每人背着 8 位数的签约金入场,在 Facebook 原有团队面前几乎等同于贴着价格标签上班。这种情况下,内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将这些人才放到同一支队伍里,要么他们产生化学反应、拿下一堆“戒指”(冠军),要么互相看不顺眼,最后一事无成。”
他补充道:“补偿团队现在肯定焦头烂额,财务部门也互相甩锅。更棘手的是,原本一些资深员工的薪水就已经高得惊人,而这些新人的待遇却又远远不在同一等级。你原以为 HR 会提前规划,让新人拿到略高于市场水平的薪资就好,结果扎克伯格突然抛出巨额签约金,搞得大家都想先拿个 offer 再说,好让公司被迫加价留人。”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下,Meta 对 AGI 的豪赌已经不仅仅是薪酬战的延伸,更像是一场“封闭集训式”的战略部署。
“我记得扎克伯格是公开说过,他相信超级智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资深 AI 从业者 Joe Ternasky 评论道,“如果你真心相信这一点,并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招募最顶尖的人才,全力以赴追求这个目标……那你为什么不召集大家,关起门来宣布:未来几年我们要拼尽全力,全速冲刺?”
在 Meta 的超级实验室中,由 Alexander Wang 领衔的角色同样备受关注。传闻中,这位 Scale AI 创始人早在 18 岁就以实习生身份加入 Quora,不仅开发了大量关键功能,还以出色的动手能力和技术判断力“吊打”了当时不少产品经理和工程师,成为实打实的“能把事情做成的人”。
后来,Quora 因资金紧张开始裁员,管理层最终选择保留年仅 18、19 岁的 Alexander,而不是那些拥有斯坦福 AI 硕士学位的正式员工,仅仅因为他在关键时刻能独立扛起任务、推动产品落地。
“所以现在,如果他负责一个冲刺 ASI 的核心团队,我毫不怀疑那群人会拼命加班,”Jordan Thibodeau 分析说,“Alexander 一直以执行力强著称,而这一次,他或许还带着点怨气——要向那些质疑他不值 140 亿美元的人证明:我能把这个项目干成。”
于此同时,研究愿景从 AGI 理想转向金钱激励,也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很多研究人员来讲,真正的吸引力从来不仅仅是金钱,而是能否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是否拥有学术自由。但现在,这些公司的“使命驱动”都开始逐渐被“财务驱动”替代。Sam Altman 此前也曾坦言:“留在 OpenAI 很值钱,我们会增长很快。”
“年轻研究员要找能做有趣课题、又有资深导师的地方;留下老将也得靠学术氛围。” Ternasky 指出,而现在的论调却变成“我们股价会涨得比 Meta 多”,于是比拼成了钱。
在这种情况下无疑 Meta 这种现金到账、薪酬透明的打法反而更具吸引力。而一旦这场竞争只剩下“谁给的钱多”,局势便会彻底失控。“既然最终都在比钱,”Ternasky 说,“那我为啥不去那个给得最多的地方?”
这场人才争夺战,正逼迫所有顶级实验室重新评估薪酬体系、锁定核心骨干、强化组织凝聚力。
(文:AI前线)

